探险,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。古往今来的探险家,将勇敢、创新、坚韧、理性、协作的探险精神传承至今。
有这样一些探险家,不但开拓了中国的探险之路,四十年来,依然坚守探险一线,为推动中国探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,并引领、激励更多年轻探险家,携手前行。
他们是“中国探险终身成就”荣誉称号的获得者:严江征、杨联康、夏伯渝、宗同昌、叶研。
严江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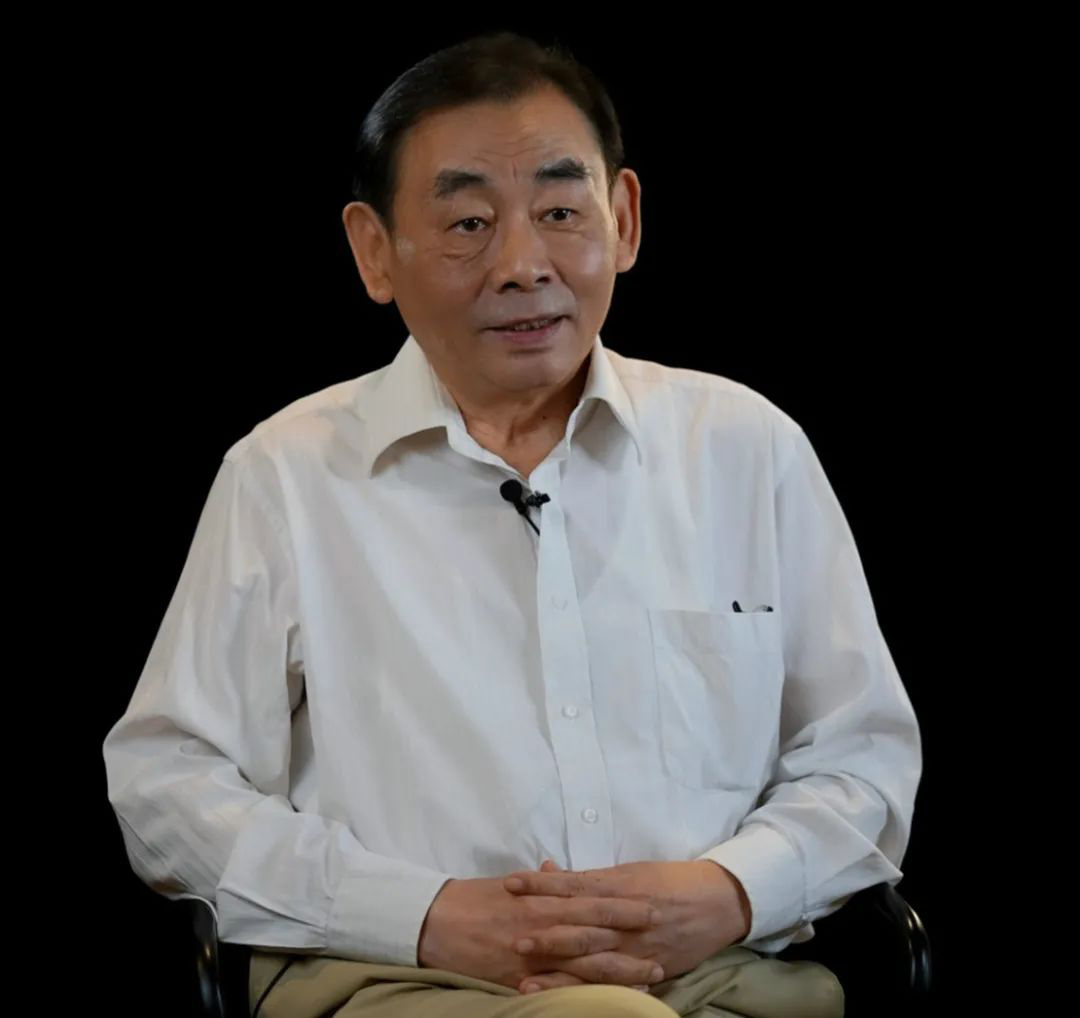
逆风执炬,敢为人先。
1993年,他创立中国探险协会,亲临探险一线,主持了系列重大探险活动。
1997年,他带着80岁的美国老人汉克斯,穿越高黎贡山丛林,抵达1943年坠毁的驼峰空运第53号运输机残骸现场。
1998年到2005年,他先后5次主导滇池水上作业,搜寻二战期间飞虎队坠落的P40战机。
历经磨难,痴心不悔。
他是中国探险协会创会主席、“中国探险终身成就”荣誉获得者——严江征。
从事山地气象专业的严江征,曾参与众多重要的野外考察,足迹遍及珠穆朗玛峰、雅鲁藏布江峡谷、塔克拉玛干沙漠,横断山脉等地。
他说:
“探险就是人类对未知的求索精神,虽然会付出孤独、疲惫、痛苦、恐惧等代价,但正是探险,让人类社会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。”
因为对探险近乎追求理想的执着,严江征克服各种困难,于1993年3月,创办中国探险协会。
中国探险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探险项目——93’沙漠之舟探险活动,由严江征担任探险队长,乘着夏季洪峰,以无动力漂流方式,沿沙漠季节性河流——和田河,顺流而下,成功完成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上穿越。
从1993年至2019年,在严江征任主席的26年间,中国探险协会先后发起、组织了:
“云南哈巴雪山探险考察”;
“滇藏文化带考察”;
“云南高黎贡山驼峰探险”;
“针对飞虎队P40战斗机的水下探险“;
“消失的要塞:乌尔古力山军事遗迹探险”;
“藏北无人区汽车探险”;
“N39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汽车探险”;
“长江当曲源头探险”;
“库布齐沙漠体验营”;
“宁夏贺兰山秦汉古长城遗迹调查”;
“陕甘青新四省(区)历史、地理考察”;
“中缅边境跨境民族——德昂族的田野调查”。
上述活动,或在探险本身,或在人文领域,均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。而其中最令严江征挂怀的,是有关驼峰航线和飞虎队的探险活动。
“驼峰航线”始于1942年,终于1945年二战结束,是滇缅公路被侵华日军切断后,由美国陆军航空兵空运部队与当时的“中国航空公司”,共同为中国抗战开辟的唯一空中补给线,为打击侵华日军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间,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8万架次,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,双方共参加人数8.4万人,共运送85万吨的战略物资和战斗人员33477人。
在这条航线,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,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,损失率超过80%。而先后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,总计损失飞机48架、牺牲飞行员168人,损失率超过50%。
这是一个用血肉、生命搭建的航线,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,付出了巨大牺牲。而驾驶当时中美两国合资“中国航空公司”53号C53型运输机的机长吉米 • 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。
1997年3月31日23点30分,严江征接到一个电话:
高黎贡山发现中航公司53号C53运输机(以下简称53号运输机)的坠机残骸,位置在中缅边境的中国一侧,距边境线仅一百多米,需派一个科考组到现场勘察。
当年“驼峰航线”的飞行员汉克斯,在1997年已是80岁的耄耋老人。他联系到严江征,表达了一同前往坠机现场探寻的强烈愿望。
当年,在53号运输机坠落后,汉克斯曾七十多次在高黎贡山上空盘旋,寻找战友的遗骸。后又受福克斯父母委托,前往高黎贡山寻其下落,但都失望而归。
带一个80岁的美国老人,到3千多米海拔的高黎贡山丛林进行高难度的探险作业,明显违反常规,风险性极大。一旦出现任何事故,各方问责,只能由中国探险协会承担。
当时的情景,严江征记忆犹新:
“汉克斯眼神里充满乞求、渴望,令人不敢与其目光对视。作为曾经参加抗日战争、帮助过我们的一个美国老飞行员,我们拿什么回报?或许就是帮他实现那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愿望。”
于是,中国探险协会正式成立寻找53号运输机的专项探险考察队,严江征亲自任队长,开始艰难寻找。
严江征主持并亲临一线,带着汉克斯,在高黎贡山丛林探寻中航公司53号运输机残骸及机长吉米 • 福克斯的遗骸。
当时的高黎贡山已进入雨季,山上浓雾弥漫,能见度至多五六米。他们一路行走在“刀刃”一般的山脊上,两侧坡度大的地方,能达到80度。虽然手里有地图,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地标,无法比对。携带的GPS在密林中也经常收不到信号。
他们在密林深处穿梭,在暴雨和泥泞中开辟道路,在推测的坠机区域转来转去,就是找不到飞机残骸。多日之后,后勤物资已“弹尽粮绝”,再加上暴雨导致衣物湿透、寒冷刺骨。
“如果停下或坐下来,很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。”
1997年6月21日14点多,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——探险队魂牵梦萦的53号运输机残骸赫然眼前。老汉克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严江征也同样流下热泪。
53号运输机见证的是人类抗战史上闪光的一页——两个在地球不同位置、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度,面对共同的敌人,并肩作战,淬炼出弥足珍贵的友谊。
2002年10月,中国探险协会策划、筹备,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的福克斯铜像,被隆重地送回福克斯的家乡——美国德克萨斯,象征斯人魂归故里。
2002年10月2日,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亲笔致信,感谢中国探险协会为“驼峰航线”53号机长吉米·福克斯树立纪念铜像,推动中美民间友谊。
2002年10月22日,由中国探险协会策划、筹备,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美国布什总统图书馆联合主办的“驼峰航线”机长吉米·福克斯纪念铜像揭幕仪式及“驼峰航线”纪念图片展在美国休斯敦布什总统图书馆隆重举行。中国航空公司联谊会、驼峰空运协会、中印缅战区联谊会、14航空队联谊会、飞虎协会及大批老兵出席活动,对中国这一系列充满人情味的安排大为赞叹。
“驼峰航线”53号机长福克斯是独生子。他来中国前也没有结婚。这场战争,毁灭了这个家庭的繁衍链条,如今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尔哈特小镇已经没有这个家族。
严江征说:
“任何一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,都值得人们铭记,不该被遗忘。
我们感兴趣的,并不是一堆冰冷的金属碎片。我们是想以这些飞机的残骸做切入点,来发掘与那场战争有关的有血有肉的人和事。”
1998年到2005年,在中国探险协会发起、组织,经外交部、国防部、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批准搜寻1942年4月28日坠落于云南滇池的飞虎队P-40型战斗机残骸探险活动中,严江征先后5次主导滇池水上作业,每次作业时间都长达数月。虽然已探明战机所在的水下位置,但受当时技术条件局限,未能打捞出水。
这架曾经参战的P40战机,是那段中美两国同仇敌忾、患难与共历史的重要物证,对世界反法西斯历史意义重大。
严江征从未放下将这架P40战机打捞出水的执念。
2023年4月27日,年届古稀的严江征实至名归,在首届中国探险者大会上获“中国探险终身成就“荣誉称号。

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为严江征颁奖
杨联康

河之所系,江之所钟。
他是河流发育史专家,也是中国第一位徒步考察黄河、长江全程的科学家。
他曾前往伏尔加河、多瑙河、尼罗河考察,享有“世界河王”美誉。
他是一生献给河流考察探险的赤子——“中国探险终身成就”荣誉称号获得者杨联康。
20世纪80年代,在黄河考察史和探险史上,有两件大事发生——一是杨联康徒步全程考察黄河,一是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等民间勇士的黄河漂流。
杨联康1961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,毕业论文题为《三峡长江发育史》。为研究黄河发育史,他自愿到当时生活条件艰苦的兰州——甘肃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工作。
1963年,杨联康工作的调查队发现了黄河最早沉积层——下五泉砾石层,认定黄河发育历史剖面——兰州剖面,使黄河发育史研究有了划时代突破。
文革10年,像杨联康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。在身陷囹圄期间,他竟然自学4种外文,写下20余万字的论文。
1979年12月,杨联康拿着“平反”补发的9千多元工资,开始筹备自费考察黄河。
1981年7月21日,杨联康正式开启徒步考察黄河的壮举。
“如果我有幸在我国实现四化的路上,做一颗小小的铺路石,我就终生无憾。”
这是杨联康1981年徒步考察黄河时说的话。这些充满时代烙印的话语,反映了杨联康的初心。他来到黄河上游的星宿海,沿马曲河步入约古宗列盆地,找到1952年国家“河源考察队”确定的黄河源头。
他记下采集到的数据后,用两个瓶子装上黄河源头水,想把其中1瓶送给党中央,另1瓶则带给他的父母。
在黄河源头,他用整整8天的时间进行考察,发现了黄河的第三个源头——拉郎晴曲比国家过去测定的第二个源头——玛曲长30.56千米。按地理学的原则,拉郎晴曲应是黄河真正的源头。
杨联康的发现,让黄河向前延伸了35.5千米。
杨联康从黄河发源地出发,没有现代化的探险设备,甚至连一顶帐篷都没有,到了晚上,他就用帆布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后睡觉。他足蹬破牛皮鞋,手持竹竿,穿高山峡谷,过黄土高原,一路攀陡崖、涉激流,风餐露宿,饱尝孤独。
杨联康为保证科考顺利进行,会向沿途各地政府索要路条。甘肃省玛曲县人民政府为杨联康开具的路条是这样写的:
杨联康同志,为完成科研项目,不畏艰险,只身一人,沿黄河徒步考察,已历时四个多月。现由我县派员护送来你县境内多柯公社,请热情接待,在食宿上给以照顾,工作上大力协助,并派政治上可靠的向导和民兵逐段护送。
杨联康徒步315天,行程5500多公里,途经沿黄9省区108个县,怀揣上百张市、县、社的介绍信,终于在1982年5月31日到达黄河入海口。
到达终点,他在大堤上跪了下来,泪流满面。
这次考察,他搜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,形成考察笔记四十多万字,成为中国徒步全程考察黄河的第一人。其后,他开始徒步全程考察长江。
1981年至1984年,杨联康以1111天的时间,徒步考察黄河、长江全程,获得全球最高河拔阶地、全球级数最多阶地、全球最厚可见黄土等重大发现,以及黄河、长江全程发育历史的系统资料。其后,杨联康通过与叶尼塞河、伏尔加河、多瑙河、尼罗河等世界知名大河的实地比较,以及与密西西比河、亚马逊河的文献比较,确认长江、黄河具全球最典型发育历史,赢得全球同行首肯。
杨联康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,提出关于我国矿产、水电、航运、水利防洪、流域开发、水产环保、旅游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文化领域的科学结论。若干年后,他的这些科学观点,几乎都被实践所证实。
杨联康认为,应该继续发展由他倡导的大河全程发育历史研究学派,以便为西线南水北调、西南水电开发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服务,为全球大河发育史的基础科学研究做贡献。
此后数年,杨联康先后徒步全程考察珠江、黑龙江,以及俄罗斯的两条大河。
至此,杨联康成为中国徒步考察江河最多的那个人。
杨联康说:
“我真正做的,不是冒险,而是要探究黄河——我们的母亲河是怎么形成的?黄河和我们民族的过去有什么关系?跟民族的现在有什么关系?我徒步就是这个目的。”
除了中国的黄河、长江,杨联康还曾前往伏尔加河、多瑙河、尼罗河等世界上多个著名河流实地考察。在探险界,他被称为“世界河王’。
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?对杨联康而言,是一生钟情于江河,一生心系于江河。
他与江河,是高山流水遇知音。
夏伯渝

一生拼搏,终成奇迹。
2018年5月14日,他以69岁高龄,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,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。
生命不息,攀登不止。年过古稀,还计划攀登七大洲最高峰、探险南北极。
他是不被命运征服的斗士——“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”的获得者夏伯渝。
夏伯渝是"2019'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"的获奖者。
是电影《攀登者》的原型,是纪录电影《无尽攀登》的主角,他43年攀登珠峰的故事令全场观众泪奔。
回忆起攀登珠峰的经历,夏伯渝说:
“山就在那里,只要你活着,就还有机会。”
1974年,夏伯渝以超强的身体素质成功入选中国登山队。
1975年,夏伯渝随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。第一次攀登珠峰的他把睡袋让给一位丢失睡袋的藏族同胞,导致自己冻伤,双小腿截肢。
因珠峰失去双腿,夏伯渝却依然眷恋珠峰。为了能够再次攀登珠峰,夏伯渝长期进行着魔鬼式的体能训练:
每天5点起床,进行力量训练;负重10公斤的沙袋,深蹲每组1500个,练10组;引体向上每组10个,练10组;俯卧撑每组60个,练8组;仰卧起坐每组60个,练8组。还要练背飞、二头肌、三头肌……
在此基础上,他还参加国际、国内残疾人运动会,并获得奖牌几十枚。
2014年3月,距离首次攀登珠峰39年后,65岁高龄的夏伯渝飞抵尼泊尔。在徒步80公里后,抵达海拔5300多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,再次对珠峰发起挑战。不料,南坡发生山难,16名夏尔巴向导遇难,尼泊尔政府取消了当年的所有登山计划。
2015年,夏伯渝第三次尝试攀登珠峰,又遭遇尼泊尔百年一遇的8.1级地震。那一年,成为40年来珠峰首次无人登顶的一年。
地震引发珠峰雪崩,夏伯渝当时正在大本营。眼看雪崩像惊涛骇浪一般滚滚而来,他紧紧抱住帐篷杆,心里充满绝望。震后,夏伯渝眼前白茫茫一片,什么都看不到。
那一次,珠峰大本营有28人遇难。
夏伯渝回忆:
“如果我的账篷搭得再往前一点,我也回不来了。
既然还活着,那我还要继续登珠峰。”
2016年,67岁的夏伯渝准备再搏一把。他拿出自己的养老金,凑足几十万元的登山费用。
这次攀登,天气不错。但在距离顶峰仅94米海拔时,突如其来一场暴风雪。一米之外,什么都看不见,雪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。脚下的路只有20公分宽,两边都是万丈深渊。
一行攀登者站立难稳,登顶的冻伤概率和坠崖风险成倍增加。
夏伯渝奋力攀登了1个小时,却只向前挪动10米。
他顺着向导手指的方向,看到远处一团乌云正在逼近——意味着天气还将恶化。
夏伯渝原本准备舍命一搏,因为他知道,无论是年龄、身体,还是财力,对他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攀登珠峰的机会。
“哪怕下不来,先上去再说。”
但转过头,当他看到5个夏尔巴向导,想到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。都有一家人,他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:下撤!
“不能因为我的梦想,牺牲掉他人的生命!”
第四次登顶成功原本已近在咫尺,却这样悍然失利,让多年来支撑夏伯渝的那股劲头一下子没了。
下撤中,他体力透支,寸步难行。只要路不平,就会摔倒;一摔倒,就躺在冰雪里,无力起身。就这样走了将近24小时,才回到大本营。
待在大本营的人,都以为夏伯渝登顶成功,纷纷祝贺。
夏伯渝忍不住流下伤心的泪水:
“老天再给我一个半小时的好天气,我就能上去……”
回到北京,夏伯渝的腿部患上严重血栓,必须住院治疗。
医生告诉他,以后千万不能再登山——血栓一旦脱落,就容易形成脑梗或心梗,连抢救都来不及。
医生让他至少休息半年,避免做任何剧烈运动。
于是,这成为他四十多年来绝无仅有“不锻炼”的半年。
别人劝他:
“差100米,也算你人生的高度了”。
他也向家人保证,以后不再去登珠峰了。
可是……
2018年5月8日凌晨5点,天还没亮,夏伯渝就从珠峰大本营出发,带着两副假肢——一副走岩石,一副踏冰雪。
一路上雷电交加,暴风骤雪。假肢上的螺丝钉掉了,幸好夏尔巴向导帮忙,在雪中找到那蚕豆大小的螺丝钉。否则,后果不堪设想。
对于用假肢攀登的人来说,最难的地方是脚底没有知觉。
“踩在什么地方我感受不到,必须用眼睛看”。
夏伯渝拿着登山杖,一路低头看着路面,根据岩石与雪层的受力方向,努力用两根登山杖保持身体的平衡。
长时间穿假肢,腿上会磨出血泡。夏伯渝努力减少晃动和摩擦——这时候绝不能出现伤口,因为他吃了抗血栓和溶血栓的药物,一旦有伤口就会血流不止。
“尼泊尔时间2018年5月14日8点31分,我终于站在梦想了41年的珠峰8848米顶峰。”
——克服千难万险,夏伯渝终于成功登顶珠峰。第一时间,他用通话机向大本营、向全世界喊话。一激动,他口误把43年说成41年。
攀登珠峰,在经历截肢、癌症、血栓、四十年如一日的残酷锻炼,每种考验都可能拖垮夏伯渝,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但夏伯渝都扛住了、坚持住了。
他,终于登上来了。
夏伯渝说:
“我觉得,自从我有了攀登珠峰的梦想以后,它改变了我的人生。而且,它使我克服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,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实、更加有意义。
我几次都想‘完了’,但我爱人跟我说,一定要平安地回来。我也向他们保证,我一定要平安地回来。就这样,我一直都在坚持,尽管后来暴风雪使我的脸、手都冻伤,但我还是一步一步地回来了。”
夏伯渝在自传《无尽攀登》中袒露心迹:
登山不是为了创造什么纪录,而是我的一种信念——就是想战胜命运。
他做到了!
宗同昌

他是故宫博物院的摄影师,是探险家,是考古学家,曾参与楼兰、罗布泊、可可西里、南极、印尼火山和搜寻“飞虎队”飞机残骸等考察探险。
他自1985年参加古格王朝考古,坚持36年,不间断对西藏阿里文化遗址考察。
2004年,他历时74天,参加“中日沿北纬39度线横穿塔克拉玛干探险活动”,成为全队唯一徒步完成穿越的队员。
2021年,72岁高龄的他,从北京自驾西藏,到达雅鲁藏布江、狮泉河(印度河)源头考察。
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
他是古稀之年仍在路上的“中国探险终身成就”荣誉获得者——宗同昌。
“塔克拉玛干”是维吾尔语,意思为“走得进,出不去”。塔克拉玛干沙漠,简称塔漠,是我国最大的沙漠和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性沙漠。
大量考古资料证明,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腹地静默着诸多曾经的辉煌。中外探险家对探究塔漠充满兴趣。
最早计划横穿塔漠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。
1895年,斯文 · 赫定组织探险队进入塔漠,最终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的行程就近乎全军覆没——活着出来的只有两个人。后来,斯文 · 赫定出版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,称塔漠为“死亡之海”。
2004年,宗同昌参加“中日联合探险队沿北纬39度线横穿塔漠探险活动“,经过74天艰难行进,日方队员先后因病全部退出,宗同昌成为全队唯一完成徒步穿越的队员。
对于这次填补世界探险史空白的探险活动,宗同昌说:
“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让我能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。一是探险,二是有机会探寻被风沙湮没的西域36国的秘密。
全日本探险协会筹备数年,日方队长成田正次先生邀请我和赵子允先生参加这次活动。
这是人类首次由西向东从最长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腹地。
我们的探险队2004年1月23日从和田出发。43头骆驼要驮载8吨装备——驮载的物资大多是骆驼饲料和饮水。
出发当天才知道,这些骆驼并不情愿进入沙漠,我们光把物资绑在骆驼背上就花去大半天的时间。队伍直到下午5点钟才出发,当天只走了2.5公里。
第一天夜里,零下25度的严寒就冻伤了一位日本队员,他被迫就近退出。
出发一星期后,跑了一头骆驼。而队长成田正次,因误将大剂量安眠药当胃药服用,药物使他几乎进入昏迷状态,已完全不能行走。为不影响队伍前行,只能将他绑在驼背上,使他永远丧失徒步穿越塔漠的机会。
行程不到三分之一时,负责全程跟拍纪录片的NHK摄制组导演又因肺部严重感染,被迫撤出沙漠。
走到克里雅河的时候,NHK另两位摄影师也因实在无法坚持而退出探险队,使NHK全程跟踪摄制工作被迫终止。而中方的赵子允先生,也因关节炎发作而退出探险活动。
过河时,一头骆驼因踩碎冰面而摔伤内脏,数天后死亡。
更意外的是,因出生了一头小骆驼,才发现驼工们把十几头怀孕的骆驼混入了驼队,严重影响了驮载能力。
在到达克里雅河前,其他队员都先后骑上了骆驼,只有我一人坚持徒步。
离终点还有三分之二行程时,也许是上天在考验我,我的腿被草蟞子咬伤,每天不得不拄棍带伤行走,还要以各种理由婉拒人们劝我骑骆驼的好意。坚持徒步,等待我的是巨大的挑战。”
茫茫塔漠,没有任何标志。宗同昌身上只有每天带的一瓶水、一点干粮,一旦找不到驼队,那就是死路一条。
回忆那次穿越,与死神擦肩的经历令宗同昌终生难忘:
“有一次我走丢了,不知道走到哪儿了——因为找不到脚印。后来,无意中突然看到一个烟头,我把烟头捡起来,撕开闻了闻——那是个刚刚扔掉不久的烟头,你能闻到很强烈的气味, 我就知道,这条路是没问题的。因为这烟头不可能是沙漠风暴刮进来或者很久以前的烟头。
最长的一次是快天亮了,才找到驼队。当时我真觉得自己又活了一次,可自己也不敢声张。
后来,骆驼多次逃跑,队员大部分生病,断粮断水很多次,谁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到哪一天,感觉已经不像是在行走,而像是从沙漠中逃离。”
最终,坚持到第74天的时候,队伍终于到达终点若羌。
“我没想到的是,在快到达终点标志的时候,队列中的全体日方队员都停下来脚步,让出一条通道,等着拄着拐杖、拖着脚步、走在队列最后的我慢慢走到最前面,让我第一个到达终点,表达了他们对全队唯一完成徒步穿越队员的敬意。”
在当天晚上的欢迎仪式上,日本的成田正次队长在讲话中宣布:
“这次成功地完成了人类首次沿北纬39度线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险活动,填补了世界探险史的空白。全程徒步的队员只有中国的宗同昌先生一人,也代表了这次徒步穿越的成功”。
新华社、央视等多家主流媒体给予重点报道。
若干年后,宗同昌回忆这次于他本人和探险界都意义重大的探险活动,说:
“也许人类大的探险活动背后,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日方队长成田正次在探险队出发前两天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,匆匆赶回日本祭奠,但又及时回到新疆,没有耽误大部队出发。或许,正因为母亲去世给他的打击,使他精神恍惚,才服错药,失去了徒步探险的机会。
而我在探险活动结束后,回到北京才知道,在我们离终点还有两天的时候,我的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。因为当时媒体报道我们探险队断粮、失去联系,身体虚弱的母亲一定是思虑过度,才没能等到我回来的那天。
后来我又见过成田先生。我对他说,'也许正是我们两位母亲把最后的生命给了我们,才让我们成功走出沙漠。'"
探险结束后,人们常问宗同昌,当年靠什么力量走出的沙漠。宗同昌是这样回答的:
这是一次中日的较量,即使是一盘棋,我也不愿意输掉!
也许,因为我有多年在喜马拉雅山中行走的经验,在沙漠中实在走不动时,我就想想在朝圣路上磕长头的人们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人类活动。
有时又自我勉励,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。
什么是大任?就是活着走出塔克拉玛干!
2022年12月,在中国探险协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“2022-2023 跨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活动”中,宗同昌担任总顾问。
宗同昌专程带领越野采风组,前往罗布泊,祭奠新疆“活地图”赵子允先生。
赵公是已故著名探险家余纯顺的向导,中日、中英横穿塔漠探险活动的向导和顾问,多年坚守在新疆,为国家寻找矿产资源。
宗同昌说:
“2004年中日联合探险队在塔漠克里雅河边,赵公因病痛要撤出,跟我告别。我都没有勇气回头再看他一眼……可没想到,这竟会是我与赵公的最后一面。”
除了中国探险协会理事、探险家的身份,宗同昌先生还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摄影师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、第七届中国当代徐霞客。
回首往事,宗同昌说:
"我是一个摄影师,同时也是一位行者。
我这辈子,到过很多一般人不容易到的地方,自然也亲眼目睹很多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风景。
我拍过很多照片,大部分都已结集出版,既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便利,也能给普通摄影爱好者、旅游爱好者带来视觉享受。
我对我这辈子还算满意。我现在身体还行,还会继续努力!"
他在首届中国探险者大会领奖时说:
我还计划至少跑10年!

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建为宗同昌颁奖
叶研

他曾参加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,到达北极点;也曾亲临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登山大本营,采访攀登者。
他加入探险队,去到高黎贡山丛林,探寻“驼峰航线”的C-53坠机。
他既有新闻人的坚守,也有探险者的无畏。
他是“妙笔生花,不辱使命”的“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”获得者——叶研。
1971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来,“新闻”与“探险”,就成为叶研职业生涯两条交织的主线。
作为记者,他要进入灾难现场、战争前线等特定场域,需要掌握潜水、攀岩等与探险有关的技术。还有一些采访,本身就带探险属性,如自然科学考察、野外历史人文考察等。
叶研说:
“专业训练并非可有可无,我高度重视专业训练。探险是严肃的事,必须尊重科学、尊重自然。因此,必要的专业训练不可或缺。
我实际上非常期待、非常享受各种探险的专业训练。”
任何了解叶研采访经历的人都会毋庸置疑地断言:他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。
然而,他更愿意称自己是“探险参与者”。
1985年、1986年赴老山前线采访,穿过炮火封锁区,进入前沿阵地乃至作战现场。危险不仅来自敌人的炮火,还有野外恶劣的生存环境。
军医说,阵地上遍布大肠杆菌。
“猫耳洞”是栖身和防御的主要场所。它搭建简便,防炮能力强,但空间狭小,不通风,不见光,一旦下雨,便会发生倒灌。
战士们还要穿越生死线,在对方火力封锁下冲过混有死老鼠、粪便、残肢、污血的泥泞之地……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泥水中,很多战士身体的局部出现溃烂,就是俗称的“烂裆”。
“我看到一个连级指挥员用三角巾兜着身体,坚持指挥作战。”
1987年,在大兴安岭火灾一线报道,他回忆现场的情形:
“我和雷收麦跟一个步兵团到古莲火场。夜间,对面的火势比较大,身后也有火情。当时部队已经一个连队、一个连队地撒开了,我独自往富克山方向去做一次观察。
跑了几百米,看清楚富克山方向的火势已经连成一条线地往这边蔓延,我赶快跑回来报告。部队也接到指挥部命令,全团就在两条火线压过来的过程中撤退。
团长让我上了一辆吉普车,干部、战士扛着工具跑。最后撤出来时,两边的火已经窜到公路。”
1995年4月,叶研参加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,到达北极点,见证了五星红旗插在北极点。
1996年5月至6月,叶研来到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登山大本营,采访。
1997年,叶研参加中国探险协会组织的“驼峰航线”探险队,寻找中航公司的C-53坠机,帮助已八十高龄的美国“飞虎队”飞行员汉克斯得偿一生夙愿。
1998年,叶研采访长江特大洪水抗洪抢险。
1998年11月-1999年3月,叶研参加中国第15次赴南极考察队,到达中山站。
2001年12月-2002年6月,叶研参加《极地跨越·两极之旅》系列纪录片摄制车队。
2005年4月-2005年9月,叶研参加《睦邻》摄制车队,任副领队。
2006年8月,叶研带队完成《睦邻》系列电视片对三个隔海邻国的拍摄、采访。
2006年11月-2007年2月,叶研参加《中阿友好万里行》系列纪录片摄制车队,任总领队。
2012年8月23日-9月7日,叶研参加《中澳沙漠大穿越》活动,任项目顾问和主驾驶。
2015年6月-8月,叶研参加《英雄当归》活动,任副领队。
“我到了,我看了,我记录了,我传播了。”
——叶研说,这是他新闻记者生涯所践行的准则。
透过记者的身份,叶研进入到很多不同的角色——“驼峰航线”考察副队长、滇池P-40战机打捞活动副队长、南极考察队科考班班长、《睦邻》拍摄项目副领队、《兄弟》拍摄项目的总领队……
在他身上,既能看到新闻人的坚守,也能看到探险者的无畏。
他说:
“在我有限的生命存续时间,我经历了很多别人的人生。这些人,在他们的行当里付出和牺牲。他们是英雄!”

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巡视员张燕茹为叶研颁奖
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
让我们再次向荣膺“中国探险终身成就”荣誉称号的严江征、杨联康、夏伯渝、宗同昌、叶研致敬,期待他们继续引领年轻探险者,推动中国探险产业做强做大,光耀世界!